王禾:话剧对心灵的感染来得更强烈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1:52:56 点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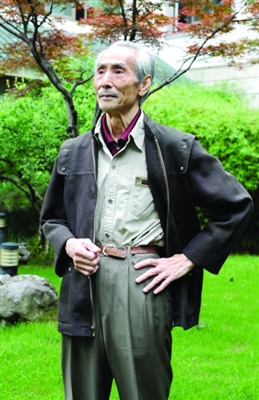 10岁时第一次接触话剧
苏周刊:您是什么时候接触话剧的?
10岁时第一次接触话剧
苏周刊:您是什么时候接触话剧的?王禾:10岁左右,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在重庆的街头,文艺表演者以演讲、广场剧等形式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艺术形式。
应该说我的童年是跟着父亲走南闯北,虽然见多识广,但也养成了好玩的天性。父亲一直在铁路上搞工程建设,记得最深的是我小时候几乎没住过房子,一直住在火车的卧铺车厢里。铁路铺到哪儿,家就跟到哪儿,读书也是。我小时候就会扒火车,火车来了我就跳上去,快到学校附近的地方就跳下来。
苏周刊:这样的经历到什么时候结束?
王禾:初中。我读书还是很好的,再加上父亲的辅导,初二跳到高一,高二我就去考大学了,真考上了上海交大,那年我才16岁,在上海解放前夕。
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电影厂门口时,几位电影明星把我叫住,问我喜不喜欢拍电影?我说“喜欢”。过了几天,他们真的来接我拍戏了。拍的第一部电影是部古装戏,我在里面演一个小孩子:挎着竹篮,里面放了几个山芋,偷偷到地牢的一个小出气孔边给里面的人塞山芋,“给你山竽吃”,就一句话,里面的人接了以后,就赶紧往回跑。CdN-wWW.2586.wang这太容易了,“一条过”。得意忘形,连接山芋的是谁演的都没有看清。这是我的第一次“触电”。
后来不断在一些电影和话剧里参加人物表演,军管会一位干部看完戏,到后台动员我参军,我就参加了上海警备区文工团。
苏周刊: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了军,父母知道吗?同意吗?
王禾:当然不同意。学校告状,说我经常逃学,父亲狠狠打了我一顿,我就逃跑了。先逃到话剧社,当时在上海有很多这样的艺术社或话剧社,多由影剧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成立,比如苦干话剧社,我记得创办人和主要演员是赵丹、王丹凤,还有新华话剧社、艺声话剧社等。解放后,这些剧社里的明星们大多成为新中国的知名文艺工作者。
苏周刊:这期间您演了哪些戏?对您后来的演艺生涯起了什么作用?
王禾:《雷雨》 中演二少爷周冲,《边城故事》里演青年技师等。和一些名演员搭档,不仅领会了“身教”,还得到他们“手把手”的指导,为我到了文工团就能担任重要角色进行了预演。 曾跟周小燕学唱歌 苏周刊:后来您加入了上海警备区的文工团,演的第一个话剧是什么呢?
王禾:那是上海刚解放不久,文工团演员什么都得演。正式参加一个大型话剧演出,叫《糖衣炮弹》,我在里面演英雄人物孙纲。之后接连演了《孙大伯儿子》《上饶集中营》,我学演反面人物。后来他们说我音色很好,问我会不会唱歌,我说会呀,唱了两句,他们觉得不错,当场决定我演歌剧《白毛女》里的黄世仁,说我不像农民,不能演王大春。我不服,英雄人物我都演了好几个,一个农民青年我演不了?团长说让这小子试试,经过试排,同意我交替演正、反两个角色。这一下我红了,又立军功又授奖,每天还能领一个鸡蛋作为奖励。接着,《刘胡兰》《小二黑结婚》《赤叶河》等歌剧都演了。
之后的几年里调动频繁,甚至几个月就调一次,反正组织上叫去哪儿就去哪儿。大的调动是福建海门,参加解放舟山群岛、一江山岛、金门列岛,仗还没打响,又点名把我调到南京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剧院共有三四百人,有话剧团、越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合唱队,还有军乐队。剧院领导说我嗓子好,叫我去唱歌,跟着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学,就是后来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我其实对唱歌没兴趣。就闹情绪,打报告写纸条给院长要求演话剧,不想唱歌。后来周小燕发了脾气,因为她觉得我音色好,不唱歌可惜了。每次上课,她就发火,“噔噔噔”拍桌子,“昨天回去叫你练的,你怎么没好好练?”我说练了,“练了今天怎么还这样?一点改进也没有?”实际上我没练。她后来去院长那儿“告状”,我们当时的院长是陈沂、沈亚威,把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叫我去下面锻炼锻炼,就把我放到了朝鲜前线回国的志愿军部队驻苏州的文工队。
苏周刊:那时您在部队话剧界也有些名气了?
王禾:我既是主要演员,又是导演,又是表演课的老师。每年都立军功。1954年,我被评为华东军区“优秀演员”之一,应该是很高的荣誉了。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好在给我定的性是“边右”,于是我就被安排去了甘肃省话剧团监督使用。 在甘肃省话剧团演了不少戏 周总理的一句话让我平反了 苏周刊:在甘肃省话剧团的那段日子还演戏吗?
王禾:这阶段倒是演了不少话剧。政治上得不到信任,艺术业务上还是得到了重用。应该说造就我今天在话剧艺术专业上的这点成就,甘肃省话剧团的八年经历培养了我。但这段日子也是非常煎熬,精神上的折磨真是一言难尽。1963年平反的时候据说是因为周总理的关心。
苏周刊:那是怎么回事?
王禾:那年甘肃省话剧团进京演出,我们的戏被调进中南海怀仁堂的小剧场给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演出。我们演的是《悲壮历程》,主题是批判张国焘脱离中央。我在剧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一位军医。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到后台来接见演员,这种事我是轮不上的。后来有一位同志叫我去一休息室,叫我在那儿坐会儿,我发现就我一人,门也没关,我看到门口有人在走动。当时心里挺紧张的。过了一会儿,那人进来通知我,跟他到隔壁会议室去。我更紧张了。到那大会议室门口,工作人员把门一推开,迎面就看见周总理,坐在大沙发上,旁边坐着我们省里的领导和我们剧团的领导,红地毯上坐着我们话剧团的演职员。周总理看到我进去,探探身子把手伸过来,我一下子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旁边的工作人员提醒我,总理想跟你握手,赶快过去。我就扑过去了。之后什么也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时,我躺在中南海的医务室里。后来医生和我们团里的同事跟我说,你小子没福气,跟总理一握手你就倒了。但我记得周总理说了句话:小同志,你受委屈了。回去以后,我就平反了。
平反后,我就不想在“甘话”呆了,因为实在不想忍受那不舒畅的氛围,尽管让我留恋的是艺术上的培养。那时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但当时我年轻,没有这样的认识。到上海没呆几天就到了苏州文化局,但苏州没话剧团,没有电影厂,就从话剧演员转为戏曲导演,可以说是转行了。
苏周刊:在“甘话”那几年时间,您演过不少话剧,哪些角色您比较满意?
王禾:《红色风暴》《林海雪原》《八一风暴》《孔雀》《甲午战争》,还有几部苏联名著《列宁在1918》《教育诗篇》,有些戏到现在还一直怀念着,也觉得比较满意。但后来大部分的证书、奖状、剧照在“文革”中被毁了,现在只残存着几张剧照。 最崇拜的话剧演员是金山 苏周刊:您最崇拜的话剧演员是谁?
王禾:金山。他和孙维世的故事,以及金日成秘书的故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金山写了著名的话剧剧本《红色风暴》,剧本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排,他在里面演主要角色“施洋大律师”,在第一届全国话剧汇演作为奉献剧目,轰动话剧界。后来《红色风暴》拍成电影,就是著名的《风暴》。
苏周刊:您有没有和金山一起排过戏?
王禾:这倒没有,但有过接触。第一届话剧汇演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甘肃话剧团送去的话剧是《在康布尔草原上》。趁在北京的机会,我们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老师请教《红色风暴》的表演,准备回甘肃后也排这部戏。我也曾向金山本人求教过“施洋大律师”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演。 话剧的表演是一种享受 苏周刊:从话剧演员变为戏曲导演,这个角色转换您适应吗?
王禾:还是适应的。苏州没有话剧团,来苏后我只好导戏曲。我做导演有个特点,话剧加唱。人家一提是王禾导的,那肯定是话剧加唱。我指导戏曲的时候要求用话剧的方式来体现戏曲人物,要求演员唱的时候也一定要动情,话剧表演的动力就是“动之于中,行之于外”。
苏周刊:演员觉得有难度吗?
王禾:开始不适应,我老是被他们骂。我记得一次去上海给他们排话剧本子改编的沪剧《红岩》时,许云峰上场时的那段,我要求演员用话剧的表演形式,拎着脚链,往下一摔,实际上也是起一个亮相的功能,然后一个大大停顿。习惯了戏曲表演形式亮相的演员怎么也演不好,三遍之后就有情绪了。我说上午就不排了,你再去想想,下午再来。他到了后台就骂开了,说“我演了一辈子的戏了,到你这儿就不会演了?我连一个上场我都不会上了?当着那么多后辈的面一次一次叫我重来。”后来我叫人把团长请来,再跟他沟通,慢慢地他领会了这样表演的奥妙。正式演出的时候,就这一亮相,底下观众“哗哗”地拍手。后来那老演员反复向我道歉,来我家时,一次给了我两条金华火腿。
苏周刊:您还拍过不少影视剧,如《水浒传》《沙家浜》,和一些名演员如王思懿、何晴也搭过戏,您觉得演戏和演话剧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哪个带劲?
王禾:话剧。话剧的表演是一种享受,包括导话剧时也是一种享受。进入角色后,体验人物的生死离别、爱恨情仇。
苏周刊;那演电影呢?
王禾:电影是分镜头拍,一次不行可以两次、三次甚至N次,而且不连惯,你刚刚入戏,导演可能就会喊“停”。有时拍这个镜头可能是很悲情的,几分钟后下来另一个镜头可能就是狂喜的。
苏周刊:那对人的表演要求不是更高吗?
王禾:是,感觉要来得快,但不是享受的,一定程度上是受罪。话剧是连惯的,你在人物里面一直游走着。享受它的悲,享受它的喜,不同的演员不同场次同样的戏会出不同的效果。所以锻炼演员和考察演员的表演功力,是话剧。许多明星被采访时问到下一部准备拍什么戏,他们有时会说,休整一段时间,充充电,演演话剧。 著名导演苏舟曾在第一期话剧培训班受训 苏周刊:上世纪80年代您曾办过大地艺术夜校和黄河艺术学院,开了专门学习话剧表演的培训班?现在还在办吗?
王禾:加上春花表演培训班和蒙特希影视艺术公司(谢晋影视学院苏州培训基地),二十多年招了近2000学员,现在不办了。其实在办这些学校之前还办过第一期话剧表演培训班。1982年,团市委主办话剧表演培训班,打听到了我,叫我做指导老师,我很高兴就接受了。就在万寿宫里面。那时候,电影特别是电视开始兴起,想当明星的年轻人比较多,我记得报名场面很火爆,30个名额,来了3000人,优中选优。不过那期也出了一些人才,比如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苏宇,现在是教授级了,还有就是著名导演苏舟,还有广播、电视台好几位主持人,都出自我那期的培训班。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是王禾“黄埔一期”的。
苏周刊:与您的培养有关。
王禾:不能说是我培养的,只能说在我这儿受了些启蒙引导。高兴的是,他们回苏探亲时,有时也会来看看我,他们拍的电影或电视剧也请我去担任个角色。 30年义务给东吴剧社排戏 苏周刊:您一直在给东吴剧社排戏,是这样吗?
王禾:东吴剧社可以说是中国较早成立的一批校园剧社之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也是苏州话剧舞台仅存的比较正常开展活动的学生剧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给他们做艺术指导,一直到现在,给他们排过戏,也给他们讲过课,陪他们熬夜,陪他们领奖。
苏周刊:东吴剧社规模如何?
王禾:每年都有新生力量加入。多的时候近百人,一般五十人左右。每年都排话剧。
苏周刊: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吗?
王禾:不是的,他们还到外校、外地交流演出,受到欢迎的也不少,得过奖的也不少。
苏周刊:近几年东吴剧社排演的情况如何?和以前相比有些什么变化?
王禾:大学生求索新事物,这是好事,但如果不把握艺术规则和本性,一味把“好玩”当创新,那就可惜了。我老了,参加的活动少了,但仍有责任提醒他们。
苏周刊:您给他们排的戏印象最深的是哪部?
王禾:《青少年的爱情喜剧》《雷雨》《心扉》等等,好多。说个有意思也很感动我的戏,就是《正在想》,是我写的剧本,讲一家三代教育工作者在思想上的碰撞。剧本给当时苏州大学的一位副书记看过后,她觉得非常好,对“奶奶”这个角色特别喜欢并作了非常具体的指导。我就鼓动学生,邀请她参演,她很高兴就接受了。后来到南京演出,比赛又得了一个特等奖。那段时间在东吴剧社掀起了一个活动高潮,大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苏周刊:在给大学生排戏的过程中您是种什么感觉?
王禾:很兴奋,很享受艺术的教育功能,我和身旁的大学生们都体会得到。我给他们义务排了30年的戏,没收取一分钱,因为这是我一生的最大的爱好。说到钱,我到现在参加了几十部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一些导演,好多都是我培训班的学生,他们问我该给您付多少报酬?我总是说我们先不谈这个,拍完再说,按质给价,给我多少我拿多少。你说我缺不缺钱,我缺钱,我很缺钱,我唯一的女儿瘫在床上三十年,家里最穷的时候,板凳全卖光,吃饭时放三张报纸,中间一张搁饭搁菜,另两张用来垫着坐。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会攒钱,早年提倡“只讲奉献,不讲回报”,现在还是这观念,我不高尚,没奉献的本事,只喜欢做事,我只要不冻着不饿着就行了。 一些所谓的实验话剧实在看不懂 苏周刊:对现在排演的一些话剧,比如先锋话剧、实验话剧,您怎么看?
王禾:现代话剧接触得不多。时代在发展,艺术也在发展,话剧也一样,国内的导演开始探索寻找新的戏剧观念和表现手法,引发了实验剧风潮。这些新的流派对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说,有时还不太容易接受,比如说《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来苏州演出时,东吴剧社给我买的票,说是一种新的形式,叫我去看。我也很好奇,想看看到底是怎么演的。演出之后演职员与观众见面会,有人介绍我,他们问我的意见。我说我没意见,因为我没看懂。再问,哪儿没看懂,我说整个没看懂。
苏周刊:您确实是没看懂吗?
王禾:确实没看懂。我到现在也没看懂。
苏周刊:那您没看懂什么呢?
王禾:作为一个戏,基本的要素总归要有吧:比如故事情节、人物、人物关系、主题思想现实意义。人家回答,不需要主题,看出什么是什么。我说没看出故事情节,那就没有故事情节。
让我更看不懂的是演出过程确实有掌声,还不是一次两次,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东吴剧社的女演员兴奋得不得了,一句台词一句话就引起这些年轻人叫好。据说在北京演出时掌声不断。掌声应该是衡量一部戏的好坏。你说没有社会价值也不对,到全国好多地方演出,也表现出关注,应该是有一定社会价值和艺术造诣。但作为我来讲没看出什么来,老了!
苏周刊:是我们跟年轻人有了代沟?
王禾:有可能。我后来打电话给我北京的一些老朋友,求教北京电影学院的王淑琰老师,他说他也没看懂。也可能就是个代沟。我们退休后和社会接触少了,见识面窄了。
苏周刊:那话剧引入了很多流行文化,他们可能也在探索一种什么东西,所以把此类剧归为实验话剧。
王禾:但孟京辉导演的其它话剧我也看过,像《暗恋桃花源》,独创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当然老话剧界以前也运用过,但林兆华用得更妙。 话剧对人心灵的感染来得更强烈 苏周刊:今年话剧节期间,苏州舞台上也热闹了一阵,苏州的观众还是蛮喜欢看话剧的,您觉得苏州话剧的环境或者说氛围怎么样?
王禾:苏州解放后没有话剧团这是我一直最遗憾的事。有的人说苏州人不喜欢话剧,我认为没有培养,当然没有人来喜欢。就像你没吃过牛排,一开始会觉得吃不惯,不好吃,你就不给他吃,那他永远不知道它好吃而且有营养。你给他吃得多了,慢慢他就会觉得这里面营养好,而且越吃越好吃。更重要的是话剧对人们心灵的感染,培养人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意识是其它剧种所达不到的。
可以说,话剧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喜怒衷乐都在话剧里了。我为什么一直把话剧当作自己最大的兴趣,就是因为话剧的作用。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靠法律制度能约束得了的,而是靠内心道德的自律。提高人性的修养,对美的追求,形成他自己本身感情领域里面的一种道德自律,你就会自我把握,用不着到时候舆论和公检法来帮你把握了。
苏周刊:您认为话剧真能产生这样巨大的作用吗?
王禾:我觉得能。
苏周刊:其它的文艺形式,比如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曲艺也可以呀?
王禾:其它的应该说不如它。有的艺术,观众更多地是看技艺,话剧不一样,既没有唱也没有跳,全是靠真情实感引起观众的共鸣,一种面对面的心灵感受。我记得那时演《红色风暴》,一个观众说连看了四遍,太震撼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施洋大律师给工人讲了发生的案情后,有一句台词:难道这是公道的吗?观众席里好几个人站起来,怒吼“不公道”。施洋又来一句:真正的杀人凶手是谁?“是那个警察局长”。这不是导演安排的,是观众由衷发出的怒吼,这就是话剧的感染作用。
我教培训班的时候,有的学员连着学四期,要知道我们那个培训班不是初级中级高级一级级递升的,每期都差不多,我们不光培训他们的表演技艺,还培养他们该怎么做一个人,所以有一个学员学了以后,他爷爷奶奶跟我们说,这个孩子好像变了,看见邻居也能打招呼了。
苏周刊:是不是因为您干了话剧这一行,您觉得话剧比别的形式对人心灵的感染来得更强烈些?
王禾:也可能。我不是强调唯一话剧能起到修身养性这一作用。我强调的是应该多多接触这些优秀的艺术形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浸润人的心灵。就会自然形成对自己的行为规范,自觉做到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