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际成:演戏无捷径
来源:不详 时间:2014/8/20 22:15:14 点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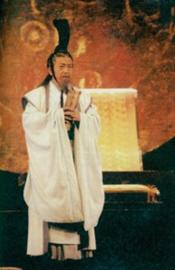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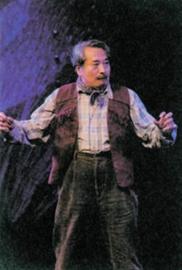

娄际成在话剧《商鞅》《榆树下的欲望》《吁命》中的舞台造型
有人说,他的身上承载了半部中国话剧史。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艺术世界,娄际成一直活跃在舞台第一线。在上戏实验话剧团演出《战斗的青春》,在青年话剧团演出《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莫扎特之死》,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商鞅》……娄际成近60年的戏剧人生,他辗转数个剧团,人一直在台上,心却永远留在了青话。 本周,年近八旬的娄际成凭借在《吁命》中塑造的吴孟超一角,第三次夺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此前,他在《商鞅》中的精湛演技,曾让白玉兰评委会打破“规矩”,删去了当时评奖条例中关于 “退休、60岁以上演员不参选”的条例……娄际成自己常说,决不走捷径;报道说,他钻研技艺锲而不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观众说,娄老爷子只需站在台上,不动不说话,看着就是种享受。cDN-Www.2586.wANg 理想 记:您是北京人,少年时只身南下来到上海,从此定居在这里生活、演戏。北京是中国话剧重镇,您为何没有想到回去? 娄:中学时我经常去北京人艺和青年艺术剧院看话剧。1950年,我上高中,参加了学校里的话剧团。当时,青年艺术剧院的一位老师来给我们辅导话剧。在他的推荐下,我去参加并通过了青年艺术剧院的考试,考官是孙维世。高中毕业时,学校又宣传服从统一分配,分配我到上海的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我去问孙维世,是留在北京还是去上海?孙维世说,“如果你想一直干这一行,就从头学起”。于是我就服从分配,来到上海学习。 1956年,我毕业后留院任教。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的提议下,学校成立了实验话剧团。此后,我就跟随着实验话剧团的发展留在了上海。我觉得不可能再回到陌生的北京去了。年少时总希望在外闯荡,因此即便有过回中戏的机会我也放弃了。 记:毕业后您留在上戏实验话剧团,演出剧目多与实验、青春、理想有关,这是否影响了您后来的戏剧观念? 娄:熊佛西建立实验话剧团时有明确方针——实验、教学、科研三者结合。没有演出任务,只要有研究课题就可以排戏,排戏也就是搞科研。 我们演过一些经典剧目,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莫里哀的《吝啬鬼》,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契诃夫的《樱桃园》,国内的经典《桃花扇》《甲午海战》等,还有戏剧学院原创的剧目《战斗的青春》。 《战斗的青春》可以说是实验话剧团原创剧目比较有名的实验剧目。实验、青春确实是我们经常演出的方式及题材,也是我个人认同的。五年的连续演出,让实验话剧团赢得了很多青年观众,所以后来领导才决定把实验话剧团交给文化局成立演出单位。可以说没有实验话剧团5年的演出经验,就没有后来的青年话剧团。 中坚 记:许多老青话人对青话都格外依恋,并说青话人和其他演员不一样。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娄:我们确实在各方面都和一般职业剧团不一样。我们是学院派,演出方法很难和一般的方法或是没有方法的方法融合起来。 区别最主要的表现在演员方面,青话人指的是50年代下半叶至60年代上半叶这十年中留下来的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毕业生。那时候我们的的确确是科班出身,属于“斯坦尼体系”,对中西文化有很深厚的修养。我们表演也是在大家的不断磨合、实践、辩论中成长的,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融合成了默契。这才是青年话剧团。 青话的排戏过程很长。从拿到剧本到分析剧本,都有详细的程序和方法。一般剧团拿起来背词,走走位就可以了。 在艺术上,青话追求的是真、热情、美。我们也有自己的三个独特风格。一是“行动的活动”。“行动”是专业名词,表演艺术是真听、真看、真感觉、真行动的“行动”的艺术,这是表演艺术的生命。二是热情优美的旋律。三是自然表现出的青春气息。 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七八十年代,都是青话辉煌的时期。此时您作为话剧舞台的中坚,您怎么看待当时前后话剧的发展和变化? 娄:“文革”前的戏剧,也就是建国之后17年的戏剧,剧目有两类:一类是主旋律的,第二类是中外经典剧目。话剧非常受观众欢迎。 “文革”后,话剧起初很热闹了一阵子,因为一批揭批“四人帮”的戏。后来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也变了,到剧场来的需求也减少了。这之后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剧本荒”。再后来市场打开,《外国文艺》《译文》不断介绍外国的文艺动态,作者和演员都如饥似渴地了解外面的东西,但是剧本不是一下子能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剧场走向了低谷,当时我们青话提出了“振兴话剧”的口号,演出了《西哈诺》《悲悼》《秦王李世民》等一系列好剧,导演、演员、剧目都很成熟,可以与北京相媲美。 到了90年代,我们的年龄大了,这批话剧力量逐渐退休、减少了。在这样的状况下,90年代的下半叶我们又进行了改组,青年话剧团和人艺合并。回过头看,也许扶持两个不同风格与追求的剧团对竞争更有利吧。 责任 记:您说,自己对青话的情感永远没有归宿。但您在“青话”消亡之后,依然是活跃在一线的演员。戏剧人都觉得您在老一辈的话剧演员中,身份转变得恰当、自然。 娄:所谓“没有归宿”实际是对青话的感情。 退休后,我自己干自己的,都是一个人面对严峻的现实。青年和中年时期我在青话度过,老年就在话剧艺术中心度过。这些年,我在话剧中心演了8个戏,其中《商鞅》和《吁命》都获奖了。戏是整体的戏,我不可能把青话的排练工作方法灌输到另一个剧组或团体中,但是我可以做到自己所要做的,坚持自己的表演方法、表演追求。对于别人的东西,我常常觉得他们准备不足,我心里替他们遗憾,但是现实就是这样,所以尽量有个包容的心态,独善其身吧。 记:退休之后,您主演的《商鞅》《榆树下的欲望》《吁命》三夺白玉兰,不知您如何评价自己在这三部戏中的演出? 娄:《商鞅》主要是对于公子虔这个人的构思:他从一个皇上非常信任的大臣,突然变成一个阶下囚,被商鞅锯断了左足,八年后瘸了腿驼了背,但是对事物的判断还是很明智的,只是性格判若两人。构思是这样,接下来就是演技的问题了。我要形体变、形态变,要爱发脾气、爱挑刺,一个不满就发火,语言声音都要变。主要的戏就是一场,要表现出这样的性格。 《榆树下的欲望》讲的是一个外国的农场主,自己把地里的石头用手搬掉,开辟了一个农场。是这样一个粗犷硬汉的形象,带有原始野味的这样一个人。关键的一段独白,他知道自己年轻老婆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而是他儿子和这个年轻女人通奸的结果,他发火,我的处理就是让他突然失声,嗓子哑了。这个在一般演戏中不太多见。 《吁命》中我的角色原型是吴孟超,他是我创作的楷模和动力,是我做人完善自我的榜样,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心里和他一种完全沟通。确实他比我大十多岁是我的长辈,但是他经历的时代,我同样经历,我对他感同身受。这个境界在我们戏剧里来说就是达到了“我就是”。 记:如今,观众说起您,都会称赞您“演技高超”。您对演技高超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娄:演员演技高超不是源于天赋。天赋条件是要的,但没有内在的感应也演不出戏,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该动摇的。 什么是演技?几句话概括:第一是在学校学习演技,第二是经历一个阶段苦练演技,第三是发挥出自己的演技,第四个是把你的表演掩盖起来。 现在舞台上说话流行说得非常流畅,语速很快,没有强调没有重音,越平淡越好。他们在思想观念上是追求生活,但是他们忘记了一条,舞台上说话是要表达人物内心,说话不是说台词,说话本身就是表演,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你要表达,你用语言去达到你的目的,跟你用形体、眼神表演是一样的,甚至你无声音无动态静止在那儿的时候也是表演。演技包括方法,演员用不用心,是否用心洞察生活,是不是用心在演戏,是不是用心在准备,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是什么都不行的。有了方法还要有心,有了心还要演技来体现。比如演喝醉酒,装醉不行,要演到真醉,那才是演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