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诗意人生——冯晓军山水画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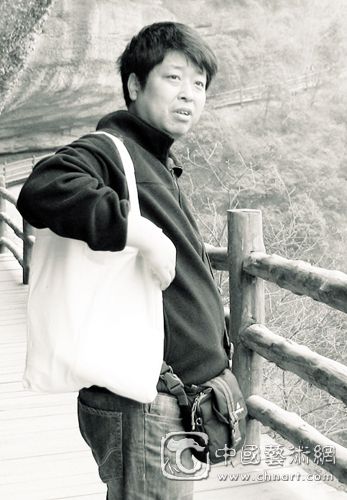
和晓军相交多年,最神往的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秦岭山中看云团”。
某年岁寒,一冬无雪。在惶惶之中过完春节,一觉醒来,窗外已是银装素裹。晓军的电话急切切打进来:进山!山坳里,冥坐孤亭,有话则谈,无话则枯坐。山峦烟树,本已让自然壮丽秀奇,又添雪之精灵,在林梢山巅舞之蹈之,怎让人麻木的心不蓦地发狂。眼前的山野林莽,在雪衣的轻罩之下,顿显飞白。晓军说,这难道不是一幅最好的山水画么?
林语堂说,大自然本身始终是一间疗养院。它如果不能治愈别的疾病,至少能治愈人类狂妄自大的病。晓军爱进山,除了为他的笔墨寻找灵动,为他的意境捕捉气韵,在我看来,还是要在山的伟大面前感受人的渺小,使自身在山野中除掉许多物欲和不必要的烦恼。进一趟山,过不多久晓军总能画一幅画出来,那幅画是在世俗的城市里勾抹出来的,落笔在夜深人静之时。画面又比先前少了躁动,多了隐逸。
知人品其画。晓军的性情颇有点闲散:在懒惰中用功,在用功中偷懒;书也读读,可是不用太用功;学识颇渊博,可是也不想当专家。这与古人的观点颇也投合:绘画是一种消遣和趣味,不掺杂功利的笔墨才能表达真我。他的这种在动与不动之间寻找均衡的生活哲学也自然体现在他的水墨之间。
在《寒宫近月》一画中,遁入眼帘的前景,水边卧石,石上生树,枝干弯曲,俯身溪流。cdn-wwW.2586.WANg平缓隆起的山峰,生发着高洁挺立的青松,层峦叠嶂向云端力争而去。蜿蜒的山路隐身在山林之间,即使危崖上的寒宫,也可觅踪寻访。但,寒宫危崖之后,却是嶙峋峥嵘的群峰,使人感到近月的寒意。《青山常在》一画亦如此。溪流叠瀑,顺山坠落;树冠繁密,根系交杂,巨石之上,两人盘憩,身在画外,却能听闻那咆哮的水声。然,头顶之上,剑锋斜刺,峭壁悬空,如层层巨浪一般,在空中肆意。
平和和峥嵘,入世和出世,神秘和亲近,在一幅画中自然结合了。它不是人为的摆布,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恩赐于生灵的结合。那种峥嵘,是我们对自然神秘力量的膜拜;那种平和,使我们能感恩自然的赐予,但最终使我们意识到,宇宙之中,自然为大!我不知能否把晓军的这种表现手法称作二度时空,但品读他的水墨,却使人往往在现实和神秘之间、肉身和心灵之间、尘世和玄冥之间,腾挪游走。
品画能知人。我尤喜晓军的山水小品。他的山水里潜藏着明显的倾向——空灵。所谓空灵,就像你喝了一杯香茗,过几分钟才能体味它的妙处。他的笔墨不猎奇、不搞怪、不无厘头,甚至想回避苍凉和悲怆。这种意境是中国人追求的意境,使人有去画里探访和小住的冲动。波澜不惊的水面,自然舒展的枝干,秀美隆起的山峰,以及一抹远山的岱影,上面行云,下面流水,中间草屋,人在天地间不觉促狭,反而享受自然的怀抱,适宜地坐卧行走,闲谈休憩。这不就是他所崇尚的王维的诗意吗?
中国的艺术家,必先有名师的传承、好学的品德和优越的修养。晓军最近常对我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的书品人品在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曾获全国头奖;他求学于科班,师从徐义生、李云集等名师,时时受到他们的指点。随着年龄和阅历的积淀,兴趣更加勃发不止。文学、历史、宗教、自然皆涉足其中。关于书画的大师专著,在他的案头随处可见。他的朋友明显多了,却也泼烦着应酬的烦恼。
晓军告诉我,只有在山里和在夜里,他才觉得适宜遂心。
我知道,在熙熙红尘,攘攘利欲之中,他尚有理想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