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浩匡庐踏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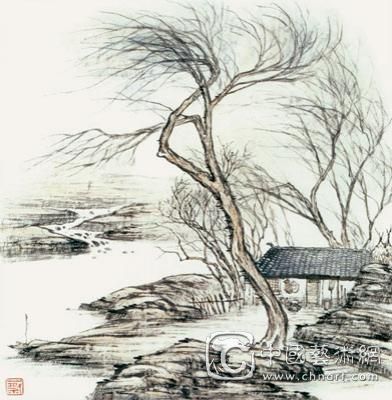
峨眉清音图
天风浩浩,日月煌煌,一股裹挟着天籁般神秘感、震撼力的气息扑面而来。画面上既有充足的细节刻画,但又绝无着力过分之嫌;风格中呈现的是笔法智巧、墨法恣情……墨色浑融中,毕现的是画家人格精神上的一种萌动。所画的山耶?水耶?这在此刻似乎并不重要,但冲击人的是一种思想引发灵魂激荡的东西。这就是施云翔近期“出人意料地向前发展”的、“有意味的”艺术形式。赏析由这气韵生动构成的西部山水景观,不能不对画家寄予作品表层和深层双重含义的思考产生极大的关注。
当代画坛既有传统功力又有过人才华,既能坚守中国画的特征又能吸纳西画优势为我所用者,云翔堪称其中之一。cDN-Www.2586.WanG在他令人耳目一新的画风中,其创意有这样的特征:广度(指技巧)上不乏灵动、博大、坚韧与包容,深度(指主观意识)方面体现学养蕴蓄的“内气萌生,外气成形”的强大主体精神,表现为画法上的则是“甚似张大千”。要之,云翔把富含的理趣、意趣、意蕴等因素和技巧都交织地掩蔽于结构新颖的山水画中。他戛戛独造的画格享誉遐迩,似领一代“彩墨画”之风骚。因素怀“从道鼎新,人画合一”的艺术理念,所以在施展青云之志的历练中,施云翔既能够做到不踵武别人,又能穷微达变、探索幽异地去探求艺术堂奥。
目前,他以对“意境是情景交融中对象外意的表达”与“境界是意境的精神高度”的深入理解,进而确认“笔墨与图式的关系则是个性化的传统笔墨决定个性化的图式”将是为获得“笔墨的解放与天地精神”圆融无碍做有益尝试的关键。
在探讨当代中国山水画的走向这个重大课题时,突出的症结问题是“关于中国画的艺术趣味与视觉化取向”的矛盾;因此“靠民族性内力发掘的笔墨转换去完成山水画的当代发展”成为云翔的明智选择,其中大有深意。从抽象水墨、水墨构成、实验水墨等水墨艺术表面看来,与原来意义上的中国画有些相似,但究其根本也只是媒介材质上的“借题发挥”而已;充其量只是以违反笔墨常规的探索完成了对中国画的有限渗透,由此导致了笔墨内涵的“约简”,实在是对传统的误读和画法上的种种舛误。严格意义上当代山水画外在形态上的笔墨构成,并没促进笔墨内在品质的提升。那些以似是而非的笔墨元素任意堆砌而成的作品,之所以造成外在形态与内在价值的背离,原因就出在对笔墨内涵与画法要旨缺少足够的认识和把握上。在这样一个艺术“共享天下”的局面中,云翔做到了“审时度势而能处高望远”,不能不承认他确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诚如南怀瑾先生所说:“知道变,而能应变,那还属下品境界;上品境界,能在变之先而求先变。”施云翔深谙“高手过招拼境界”的哲理性,于是宁可放弃一部分施展空间,精神上再度回归“笔墨家园”,敢于直面打破笔法的“旧世界”,并建立一个“新秩序”的挑战。他体察到,不可勉强地将用笔泛化为轮廓线、将用墨泛化为明暗调子,而是要重视书法与画法的有机联系;深知所画作品的笔墨意义必然大于形象意义的道理,探索耐人寻味的笔情墨意和绘画元素的内在之美。他在构思作品时,想象从不囿于固定的模式;这个能力缘于其懂得“境界包罗万象,但不被万象包罗”这个至理。云翔凸显了一位当代中国画家的良知,超越于陈腐与造作,摒弃了平庸与短见,直入现代审美转换期的深处,具有较强的当代画语的艺术品位。他正在做的思考与实践,无疑可以被视为一种系统化与学术性的文化现象,颇具研究价值。
“无工夫不足以适道,极其道,又必须忘工夫”,也是体现了云翔丹青之学的内蕴。试析他的前阶段作品,可以见出不同的取向:一是源于西法学习与视觉观念。因此,其作品中空间的呈现,每适应神游者精神的飘移而自由构置;景观的描写,亦无论画名山大川,还是写荒村野渡,都追求细节真实与整体理想化的统一。二是对景写生与回归造化。他用民族传统的画法写生,认为对景写生易得山水的骨体,师造化才能理解大自然的内在精神和千变万化,才能使造化为我所有、与画家的精神境界合而为一。三是题材的经世、功能的致用。这表现在以艺术为人生宗旨,以表现时代精神为要求,着眼于大众的生活,赋予山水画新的功能。一番为学日增、为道日损的体验后,他体会到山水画意境、丘壑(图式)和笔墨三大要素。于是,施云翔一方面致力于挣脱传统笔墨技巧对模山范水的束缚,一方面强化山水画作品的感人力量在于创造意境这个理念。一旦弄清意境创造有赖于真情实感的投入,笔墨韵律更是感情个性外化的道理,创作的契机、灵感的降临则不期而至。实现这一步的跨越,艺术题材的“出世”与“入世”、艺术基本功的“临摹”与“写生”、艺术源流的“师古人”与“师造化”、艺术境象中的“造化”与“心源”和“图真”与“造意”、艺术精神是“群体意识”还是“自我表现”、艺术功能是着眼于“经世致用”还是着眼于“精神超越”、文化价值观念是“天人合一”还是“物我两分”,这些让人备感困惑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且有“芝麻开门”的快意。探索一种对自然物象的感受达到一个高层次的审美层面,是云翔今后为之奋斗的目标。审美标榜艺术的向度,“天地境界”也可称为“宇宙境界”,乃是公认的艺术最高境界。能够进入此种境界的艺术家,必然是以凌空高蹈的博大襟怀面对现实、观察万物、体悟人生,从而在作品中开创出更宏阔的诗性精神空间,云翔作如是观。元人山水侧重于心境美,云翔似乎更贴近这样一种作为“心画”而不是作为“视觉艺术”的范畴。其近作表露的“恣纵线条倾情愫,墨渖淋漓抒豪情”等迹象,无不透析出画家内在心灵藉以传达的诉求,也即画家主体世界最敏感最自由的状态进入了艺术创作天地的生命律动。我们在投入此语境时,顿生精神感受上的共鸣;若能领会作品中的观念形态,反过来又丰富、充实了先前的感受。根本上讲,从描述绘画的本体存在,进入对作品意义的认识和阐释就是解读。这些是我们从云翔的绘画中都能获得的。那些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参照呢?我认为,他在用绘画的方式进行哲学认识论的探讨(并不意味着他要当哲学家),其课题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及认识方式的认知。他选择了笔墨和图像这两种语言作为探讨认识论的工具。他力图沟通这两种语言,从而在语言本身和被语言所表达的对象之间,发现二者相互转换的契机。他是哲学的、思辨的、理性的,在画中阐释个人的感悟。在这样的前提下,当我们有意把不同风格的流派相参照,不难看出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同的艺术精神和文化特征。
还是以西部题材作为讨论的对象。西部绘画已经经历了一个渐趋深化的历程:最先是偏重于主题性或偏重于风情性,之后陈丹青的“人性视角”与周韶华的“文化视角”是一大推进,继之而来的各种范式成为延伸。经验告诉我们,在绘画上,一种画风发展到极端,常常会有另一种画风来制衡。当然,这本身也有个“同能不如独诣”的道理使然。若可以用“文化生态平衡”来形容的话,云翔的笔墨强势力量应该而且能够占一席之地。他极具个性魅力的笔墨功夫,足以展示宏大气势的“西部精神”,而这片广袤地域蕴含的潜质也正符合云翔作大块文章的要求。为了体证自身的感悟,施云翔对民族思维的奥妙一再深入,对传统文化进行解码,得出读解的内涵:一是作为一种美学观念来看,二是作为一种生命意识来看,三是作为一种哲学观念来看。这是入其堂奥,明了中国美学中的绘画审美意味是由意义到意象、到意味的依次递进的三层次。惟其如此,才能完成量变到质变的意义。他的创作态势首先是紧扣当代社会大文化背景下的主调,自觉地把笔墨精神引向博大雄奇的艺术创作佳境。这过程中,他既完成了笔墨的“凤凰涅槃”,同时又塑造提升了自己的人格精神。在西部题材的试验田中,他可以发展自己艺术积淀下的经验,以及在艺术修养方面的再积累和综合多种艺术的审美容量,使其成为既不离开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想象空间和造型观念的源头,也提供了新的探索和新的创造基点。要实现这个目标,创造的三要素有:一是创作者个人的独特的人格精神,二是创作者所归属的那个文化的特质,三是创作者所属的时代精神。显而易见,传统派在三要素中缺乏个性与时代精神,西化派则缺乏个性与民族色彩。中国书画讲的“形”、“神”是辩证法,且以“中”为原则。老子的“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意为不走极端、不过分;儒家提倡“中庸”;佛家反对“边见”(片面观),极尊“中道”。这些观念运用到笔墨上,即可认为在各对矛盾中,两个极端间有着广阔的活动余地,这正是艺术家可以纵情驰骋的疆域。有了对生命的全新感悟,云翔遨游在一种将知、情、意和谐浑融的美妙的生存境界中;由此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本质上区别了那种现代审美意义上去追求现代感的作品。
纵观云翔的艺术成长过程:在叠层累积而成的每个时期的每一次变法,都是他丹青之魂的重塑;正是在这一层层累积的过程中,作为中国画形式“基因”的笔墨手法日臻化境。云翔艺术天赋中彰显的心理上、情感上的非凡特质,一旦以“中国画笔墨精神的现代意义”为旨归,那么,以笔墨的突破程式引起社会审美经验广泛更新为旨趣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风格,就是他精思极虑的中国山水画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