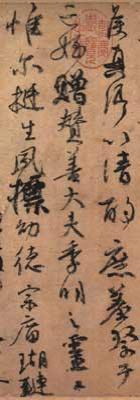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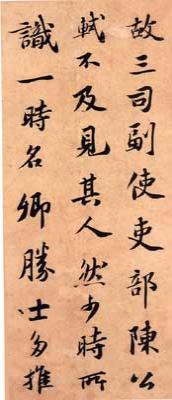
除上述之外,见于记载的两晋书家多为江左世族,这一事实在《阁帖》中也有鲜明的体现。虽然他们留在《阁帖》里的只是片楮寸笺,却无异于鲁殿灵光,同样璀璨夺目。他们与诸大家一起,为我们奏响了书法史上一个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阁帖》的整体结构。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伪迹居其大半,价值略逊。第二卷和第三卷几近全部为晋人书。据容希白先生《丛帖目》记,除去少量前人鉴定出来的伪迹外,此二卷仍得晋人37帖之多。cdn-Www.2586.waNg而其作者,复集中于王、谢、郗、庾、卫诸族,尤以王氏为众,翩翩佳子弟,多右军近支。这37帖,兼以第六至第十卷的“二王”书,琳琅满目,鸿篇巨制,无可争议地标榜着以“二王”为核心的晋人法书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更由于这种地位是建立在汉字的转型期和书法的成熟期,旗帜高张,所以无疑是不可动摇的。接下来的第四卷,略及南朝,大半为唐人书,共21帖,加上第一卷唐太宗、高宗书31帖,足以表明晋、唐间书法的发展轨迹。这两卷可信度极高,特别是唐二帝帖,无一伪迹,且篇幅之大,为《阁帖》之冠。盖北宋去唐未远,唐人真迹大量存世,既容易获观,鉴别难度也相应较小所致。
通过以上对《阁帖》的分类排列,我们不难看出,北宋时期,帖学的地位十分牢固。当然,在《阁帖》之前还没有“帖学”这一概念。此前虽有南、北之议,但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远远没有达到理论的高度,遑论所谓碑学。有宋一代,书法一道,始终坐帖学之春风,舒适优雅地成长着。“宋四家”中,苏、蔡自不必说,即便自运更多的黄、米,观其少壮之作,也是温雅有度、婉转多姿,无一笔不自晋、唐来。《阁帖》的体系,正是承袭着这一传统,专以晋、唐为矩矱。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人们往往对《阁帖》“排斥”颜鲁公迷惑不解,似乎可以于此问津。鲁公同样自“二王”出。试观其最负盛名的《祭侄文稿》,何尝不为“二王”嫡系?况且,作为有宋一代(狭义地说,就是《阁帖》所处的北宋时期)最具典型意义的书家,“宋四家”或多或少都研习过鲁公的书法。因而,我们是否可以做如此推想:《阁帖》的编辑者并非否定鲁公的大家地位,而是以鲁公作为“二王”的流亚,在《阁帖》这样一部以纯正的“二王”趣味为取向、具有最高权威的学术专著中,将其忽略不计呢?
